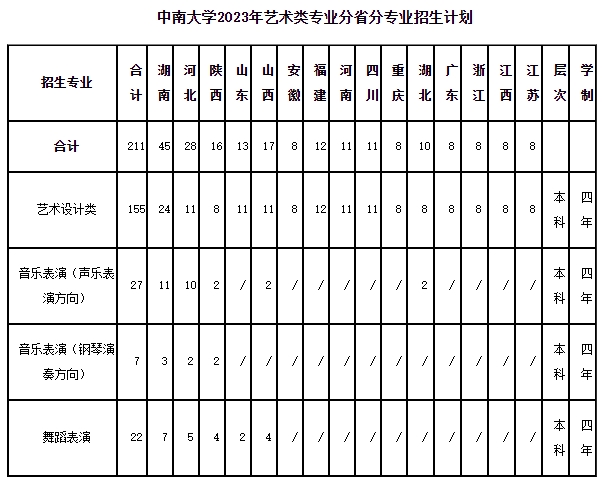老北京裝裱手藝
裝裱藝術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民族特色,書畫墨妙必須經過裝裱才便于收藏、流傳和欣賞,因而裝裱技術的高低,綾絹色彩的選擇與裝裱形式的設計直接影響到作品的藝術效果;歷代書畫珍品,如已糟朽破碎,一經精心裝裱,則猶如枯木逢春,一些珍貴畫文物因此不致湮沒失傳。
揭裱字畫也稱裝裱字畫,古老的名稱叫裱褙。北京揭裱字畫行業,都自稱是“蘇裱”。傳說是從蘇州傳來的手藝。明代有位湯勤,乾隆時有位徐名揚,他們是從蘇州來京城的揭裱字畫的藝師,聞名于當時的文人、士大夫,甚至皇帝。他們揭裱字畫技藝高超,世代相傳,精益求精。到了光緒年間,蘇裱字畫手藝之精巧,出神入化,舊字畫碎破到不可分辨,甚至糟脆到呼吸即能吹散的程度,仍可蘇裱如原狀,可謂是業界一大絕技。一般來說裝裱新畫容易,但揭裱古舊書畫則是要很高技術的。民國年間,北京裝裱業大多在東裱褙胡同和琉璃廠一帶。前者以糊頂棚、售南紙、做燒活居多,而琉璃廠的裝裱鋪才是真正的書畫裝裱行,其主要有劉林修的竹林齋、崔竹亭的竹實齋、馬霽川的玉池山房、張成榮的寶華齋……
現代的著名書畫鑒定家王禹平學徒于玉池山房,裱畫大師劉金濤學徒于寶華齋,裱畫名家崔竹亭學徒于竹林齋……可見是名師出高徒了。琉璃廠有20多家裱畫鋪,光緒末年時,竹林齋、竹實齋最出名,民國初年以來,玉池山房最著名。劉林修和崔竹亭合伙開竹林齋裱畫鋪,分手后,崔竹亭經營竹實齋,劉林修獨自開辦竹林齋。他們的手藝都好。經營字畫古玩鋪的掌柜們,給他們二人起個綽號:“劉二寡婦”、“崔三娘兒們”。
為什么兩位男子漢有這樣的外號呢?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干活心細手巧像婦女,另一方面是他們的音容笑貌像女人。劉林修見人沒笑容,臉總是陰沉著;崔竹亭說話慢言細語,嗓音似女人。他們揭裱字畫有絕活,油漬碎裂的舊字畫,經他們的手,恢復原樣;填補殘缺,看不出破綻。馬霽川在光緒三十二年先在竹林齋學裱畫,后在竹實齋跟崔竹亭學手藝。他把劉林修和崔竹亭的手藝、絕技學到手,1920年在南新華街長春會館內開設玉池山房。玉池山房裝裱名人字畫,也經營字畫。馬霽川的手藝精妙,玉池山房裝裱字畫很講究質量,達不到質量要求,不交貨,贏得了信譽。當時的北京政府及以后南京政府的要員、書畫家、收藏家林森、于右任、張學良、張伯駒、張大千、溥心畬、徐悲鴻、齊白石等,都知道馬霽川的名字。馬霽川給他們裝裱字畫,也做他們的字畫生意。張學良一幅珍貴的手卷畫,日久受潮,畫面反鉛,白臉人變成黑臉,經玉池山房整修、裝裱,恢復原樣;于右任收藏的宋元畫,年久碎裂,也請馬霽川加工修復。老北京裝裱的手藝是師傅傳徒弟,學徒要先拜祖師爺,誰是祖師爺說法不一,有造紙的蔡倫,有造字的倉頡,有畫圣吳道子,也有大儒孔夫子。學徒期間要練毛筆字,學打算盤、練記賬、學畫格式、形制,熟悉綾絹……
書畫裝裱十分注重內在質量,這就要求書畫裝裱師有全面的修養和深厚的功力,這樣才能使書畫家的作品更好地得以完售,從而提高藝術魅力和觀賞力,在長期的合作中許多收藏家、畫家、書法家都和裝裱師結成了很好的朋友,如:張伯駒與王華軒,吳作人與劉金濤……
新中國成立后,裝裱不僅繼承了歷史上好的形式、風格和技法,而且在整修揭裱古代殘破作品方面開創了新的途徑,為保留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做出了顯著的貢獻。諸如將巨幅大畫《江山如此多嬌》以及長達十余丈的《首都之春》手卷等,裝裱得莊重大方,平正堂皇,堪稱裝裱史上別開生面的創舉。俗話說“亂世黃金,盛世書畫”,如今在書畫熱、收藏熱的推動下,裝裱業也快速發展,很多畫室、畫店使用了裝裱機,15分鐘即可裱一張畫,但裝裱機只能干“粗活兒”,要求較高、難度較大的畫,還是要靠手工裝裱。作為一門手藝,隨著一批老藝人的去世,裝裱業出現了人才斷檔,很多畫店苦于找不到合適的手藝人,而不敢把名畫拿去裝裱,那種枯木逢春、出神入化的裝裱故事,只能留在傳說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