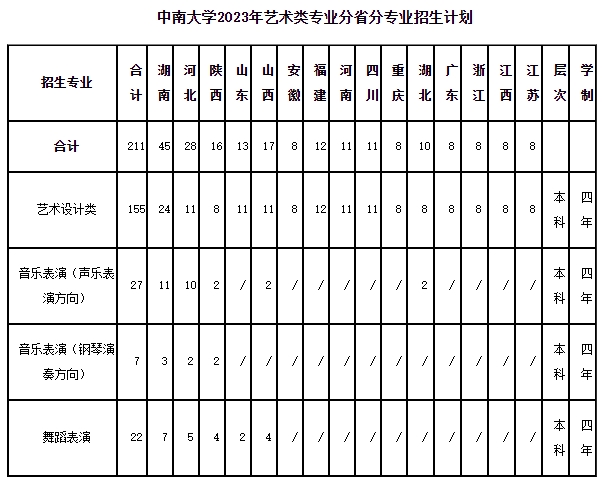1945年以來的西方雕塑(一)
前言:二十世紀后期的雕塑
在西方文明史中,雕塑這門藝術在傳統中所充當的角色有限:它具有宗教性,作為宗教崇拜的一種媒介和膜拜的對象一直為宗教服務;它具有紀念性,作為著名人物或事件的紀念物,也許是一個城市或國家的象征;此外,它還具有裝飾性,大至建筑工程小至家庭室內裝飾它都側身其中。到了20世紀下半葉,雕塑的這些職能雖然依舊存在,但在最近這幾十年中已經逐漸減弱。其中的一個原因在于,那種過去曾經作為宗教侍仆的藝術現在其自身變成了世俗社會中的一種宗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1930年發表的《文明與缺憾》一文中就曾預言到這一發展趨勢。
1960年代以后的雕塑作品,絕大多數是為了在博物館里展出而制作的(那些時常受到貶謫的室外雕塑公園,僅僅是博物館建筑的一種延伸)。在最近的三十年中,博物館的發展令人矚日,這顯然與雕塑創作的興盛及雕塑在視覺藝術的前衛運動中的重要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相應地,對于雕塑家的資助也越來越多地來自于各個博物館,或是少數幾個私人贊助者,這些人相當富有,實際上他們所收藏的當代藝術品本身就足以建立起博物館,無論它們是否向公眾開放。當然,這些收藏品與過去的那些著名藝術收藏品不同,現在基本上不把雕塑作為裝飾品來看待。
在博物館里,20世紀雕塑的職能表現在一些不同的方面。有時候,它試圖表達某一特殊的,游離于自身之外的含義--一種對歷史或時事的見解。這種現象反映在參加1953年國際"無名政治犯"比賽的入選作品中。(這種情況比人們想象的要少得多)。還有時候,雕塑又成為凝固某一特定情緒狀態的手段--奧古斯特·羅丹如果活在世上一定會對此大加贊賞并認為這才是正統的雕塑。然而,20世紀雕塑更多地強調唯我主義,它們僅僅是對于藝術制作過程,對于一件藝術品在某一既定空間中產生作用的方式,或僅僅是對于"藝術"觀念本身提出一種注釋。
前衛雕塑在宗教性方面走得更遠,在博物館的環境中,它也將自己變成一種圖騰式的物體,或是某一圣物。當今所有前衛運動的藝術評論家們必定會熱衷于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對藝術家們所涉及的題材進行"解釋"。然而,這看起來既悖離于藝術家的初衷,又悖離于觀眾的要求。藝術家們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諸如形式的奇特連接,材料的出人意料的組合。試圖創造出一件能夠產生心靈震撼的作品,正如非洲偏僻部落的面具所產生的那種效果。在這一過程中,藝術家所遇到的困難在于他們缺少部落藝術所具有的那種能夠引起通感的集體意識。然而,為現代社會創造圖騰的努力卻從未中斷過,這的確證明了人類對神圣感和神秘感的永遠追求。
對于現代派運動來說,那種認為對藝術作品的最佳理解來自于感情突發瞬間的想法并不奇特。這種思想的直接根源是19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而早在中世紀就有過類似的看法,認為靈魂對于上帝及其世俗表現形式的信仰可以激發起靈感。浪漫主義還與另一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正是他們開始將人們的注意力從藝術品轉向藝術品制作者自身;正是從浪漫主義那里我們繼承了如下思想:藝術作品并非一件獨立的實體,它更應該被看作是其制作者個人的"天才"的表現,但最近幾年中出現更深一步的轉變--一些藝術家成了他們自己的作品--從而使作者與作品融為一體,無法分辨。這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德國雕塑家約瑟夫·博伊于斯,隨著事業的不斷發展,他越來越多地扮演起現代薩滿教巫師的角色。博伊于斯既己去世,他那些陳列于各博物館里的作品幾乎無法作為獨立的實體表現它們自身的美學價值。這些作品更像是中世紀教堂中供人崇拜的圣人們遺留下來的圣物,留在那里經受考驗,看看對它們的信仰是否能流傳后世。這一點似乎又反過來取決于我們將來對藝術品所持的態度。而在目前階段,人們對藝術品的概念及其使用方式的看法正以西方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而劇烈地變更著。
就目前的情況看,人們不得不說實際上任何東西都可以被稱作"雕塑",它不僅包括傳統材料(木頭、石頭、澆鑄金屬)制作的三維形式,而且還包括了照片、圖表、口頭陳述甚至雕塑者本人的行為和表情。這一運動的真正支持者還是那些參觀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公眾中的成員(他們的數目在不斷增加),而其經費主要來自于支持這些機構的公共或私人的慈善基金。隨著這種雕塑創作越來越注重于試驗傾向,它也就會越來越多地依賴于機構而不是個人的贊助--這種現象恰好與20世紀初期現代派運動剛剛開始時的趨勢相反。
早期現代主義雕塑
視覺藝術中的現代主義無疑是由畫家而不是雕塑家所發起,早期現代主義思想則是在各種繪畫流派互相競爭中產生的。無論是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還是表現派藝術家都注重于平面,這種狀況只有在俄國構成主義者那里才有所改變。這種在繪畫中而非雕塑中注重平面的現象有幾個原因,首先,19世紀雕塑傳統的衰微沒有為激進的藝術家們帶來多少發展的契機,相比之下,當時的前現代主義繪畫卻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19世紀的雕塑界中無人可與保羅·塞尚、文森特·凡高或是保羅·高更這樣的畫家相媲美。羅丹雖然是向現代主義過渡時期最偉大的雕塑家,但他仍維持著與官方藝術界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官方藝術正是野獸派及其后繼者們所反抗的對象。
繪畫占據優勢的第二個原因在于,現代主義在其初始時期基本上是精英的藝術,它將自己面向少數而不是多數,那些激進的新藝術家們制作的作品通常規模不大,并且只是用于個人欣賞之用。意大利未來主義者倒確是有一些反映大眾思想的藝術構思(盡管主要是在建筑而非雕塑領域),可是他們卻從未有機會把這些構思付諸于實踐。俄國的構成主義者通過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聯系,賦予現代主義藝術以大眾化的職能,井同時將其與左翼政治等同起來。但是,由于當時的情況,他們也像未來主義者一樣,很少有作品存留下來。弗拉基米爾。塔特林的作品《第三國際紀念碑》(1918年受蘇維埃美術部委托而設計并可能是構成主義最著名的作品)似乎命中注定無法完成。
盡管機會很少,但當現代派或半現代派雕塑家真正為公眾設計作品時,他們往往會引起激烈的爭論。阿里斯蒂德。馬約爾的作品盡管現在看來既便用古典標準來衡量仍很保守,但在當時卻遭到了公眾團體的數度回絕。由德國人恩斯特·巴拉奇制作的感人的紀念碑盡管被豎立起來,卻激起了納粹分子的極度仇恨,他們不僅一上臺就清除掉了這些紀念碑,還將巴拉奇列為特別迫害的對象。雅各布·愛潑斯坦的創作生涯中記錄著一個接一個的抨擊。他的作品中受到最激烈攻擊的有位于巴黎的貝爾拉雪茲公墓為奧斯卡·王爾德所作的墓碑;《創世紀》;以及在倫敦的兩件委托作品:豎立在海德公園里的為紀念作家W·H·胡森而制作的麗瑪塑像和為圣·詹姆士倫敦運輸大樓而作的《夜》和《晝》。盡管他們極富才能,但無論是愛潑斯坦還是巴拉奇均未能列入一戰期間最"前衛的"藝術家行列。如果我們將他們和其他人相比較,比如與他們同時代的超現實主義者相比較的話,那么他們在前衛派中就相對顯得溫和多了。
也許是由于雕塑界的保守促使了第一流的現代派畫家在三維空間中一試身手。現代派早期最前衛的雕塑家是亨利·馬蒂斯,他在其諸如《奴隸》這樣的作品中既從羅丹那里受到啟示又從塞尚早期作品中學到了形式處理方法。作為一個雕塑家,幾乎他所有的作品尺寸都很小,與大多數早期現代派藝術所設想的家庭環境相適應。未來派畫家馬姆伯托·博喬尼也創作出一些極富新意的雕塑作品,可惜他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次騎馬事故。帕布羅·畢加索最初嘗試雕塑創作時相當謹慎,只是在立體主義出現之后他才尋找到了他畢生為之奮斗的創作方向。拼貼法的發明確立了畢加索作為一名雕塑家的身份,這一創新表明拼貼法在三維空間與在二維空間中同樣有效。畢加索對于拼貼的興趣使他放棄了已有的材料。當他制作雕塑時,任何東西都可以拿來應用,從一塊廢棄的鑄件到一輛玩具汽車或是一輛自行車的車座、車把。他的三繼創作甚至比他的二維創作更多地包含著一種不斷的變形過程和思想、概念、意象的隨意交合。畢加索似乎一直認為相對于他的繪畫來講,他的雕塑創作是一項更為私下的活動--這與這兩種表現方式的傳統狀況正好相反,他的這種看法一直持續到相當晚的時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畢加索的很多雕塑作品還無人知曉并且被隱藏起來。二戰后,他的一些想法迅速流傳開來,特別是在他的西班牙同事朱里奧·岡薩雷茲幫助下完成的焊接鋼鐵試驗。然而,盡管作為一名畫家畢加索一直是其同代人心目中的中心人物,但作為一名現代派雕塑家他卻游離于主流之外。
激發藝術家們制作出一種新的"立體派"雕塑作品的,不是畢加索的雕塑,而是他以及喬治·勃拉克創作的繪畫和平面拼貼作品,這些作品比雕塑更易見到。這些藝術家包括杰奎斯·利普奇茨和亨利·勞倫斯。這兩位藝術家的早期作品受立體主義在平面上實驗的影響非常大。他們的最初嘗試大多是浮雕而不是完全三維的,而且浮雕中交迭平面的使用也是立體派繪畫中一種裝飾性的堅實結構的翻版。在后來的作品中,如利普奇茨的《歌中之歌》,他們找到了一種擺脫這種尷尬處境的方法,即越來越多地采用曲線和不規則形狀,因而他們的作品不易被認出是立體主義的。
有一位完全獨立并富于開創精神的雕塑家其作品偶爾也帶有微弱的立體主義色彩,他就是康斯坦丁·布朗庫西。出身于羅馬尼亞農民家庭的布朗庫西終生保持著獨特的民族特色,他主張采取盡量簡練的手法,同時廢棄模型的制作而直接在石頭或木頭上雕刻。他的作品《吻》(原件1908年)是在一塊材料上表現兩個人緊緊擁抱在一起,這件作品表明了他與當時尚在初期的立體主義運動的緊密關系。其后期作品仍然很簡練,但形式有所不同,作品雖然保持了原始的自然形狀,但已經被簡化到再也不能簡化的程度。在布朗庫西的一些雕塑作品中,比如《波嘉尼小姐》的頭部(與《吻》一樣存在好幾種版本)也使人想起"裝飾藝術"(ArtDcco)的風格。隨著他的系列作品《空間中的鳥》問世,布朗庫西終于超越了他曾經恪守的自然的簡化原則,而試圖尋找一種可以顯示物體正在運動的形式,也是物體最真實的本質。
在現代派早期的雕塑中,最重要的創新莫過于畢加索在二維和三維拼貼中對"拾來的材料"的使用,然而其含義卻與畢加索自己所表明的不同。馬歇爾·杜尚的"現成藝術品"的發明對現代派雕塑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一直到二次大戰后才被充分認識到。杜尚將日常生活中的尋常物品直接拿來使用,例如1914年創作的《瓶架》,并將它們命名為藝術品,認為它們應該像正規的雕塑一樣被展出和觀看。結果引起了對于歷代沿襲下來的全部雕塑審美觀念的質疑。
杜尚的直接繼承者是超現實主義者,他們的雕塑手法相對杜尚來說不那么激進,他們仍然創作三維雕塑作品而不僅僅在周圍環境中尋找物體為藝術品。和畢加索一樣,超現實主義者們經常使用廢棄的材料制作三維作品,但即使是在與超現實主義運動有些關聯的時候,畢加索也往往是首先對其所發現的形式感興趣,而超現實主義的重要成員卻主要著迷于日常物體的不和諧并置所引起的組合變化。超現實主義者們常常不僅制造不和諧的并置組合,而且還擺弄明顯不合常規的材料,這方面的例子是米萊·奧本海姆的作品《長毛的茶杯》,它常常被認為是最典型的超現實主義作品,然而我們卻很難將其列入雕塑之類。與完全拼合的作品相比,制作可塑形態作品的念頭在超現實主義者的意識中形成相當晚。漢斯·阿爾普就是首先制作拼貼畫和在涂色木上做浮雕,后來才開始創作生物形態的石頭雕刻品,這些雕刻可以被看作是對身體的某些部分和對植物發芽、結果的隱喻表現。
超現實主義雕塑家們的創作面貌不同,他們將這一區分帶入了持續至今的雕塑傳統之中。一些現代雕塑作品要求人們單純從形式上去理解,而另一些作品則對形式興趣不大,甚至毫無興趣,它們完全靠喚起觀眾的聯想而打動觀眾,批評家們感到要對這兩種風格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是非常困難的。
就其所產生的直接效果來講,超現實主義的雕塑創作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幾乎是一戰期間唯一的雕塑活動形式,代表著一種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真正嘗試。與繪畫不同,大多數雕塑作品仍與過去文明保持著某種聯系--這種新舊之間的交替更具吸引力,因為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的快速發展極大擴寬了獲得靈感的來源。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畢加索在繪畫中復興了新古典主義風格,雖然他本人馬上又放棄了這一風格,但卻使很多二戰期間的雕塑家對此格外著迷,甚至包括那些基本上贊同現代派的雕塑家。這種風格還因其與昔日輝煌的帝國時代的聯系而倍受獨裁統治者的青睞--像在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和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在德國納粹時期最成功的雕塑家是阿諾·布雷克,他是馬里諾·馬里尼的親密弟子之一,后者為希特勒在柏林的新帝國官邸創作了許多健壯青年的形象。與新拼貼派(Novcccntogroup)有關的意大利雕塑家也以某種形式的新古典主義風格進行創作,但同時他們還受到伊特魯里亞藝術獨特風格的影響,并從他們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家那里繼承了不少東西。他們中間像馬里諾·馬里尼和加柯莫·曼祖后來成為戰后時期具有國際聲望的雕塑家。
與這一持久的新古典主義潮流悖逆的方式之一--至少當時許多的前衛派雕塑家這樣認為--是從原始藝術和古代藝術中尋求靈感,而且往往是從那些與歐洲主要傳統毫無聯系的文化所產生的藝術中吸取。前沿的現代派藝術家們與其他一些人首先認識到非洲和大洋洲的部落藝術家們的創作已不僅僅是出于好奇,他們的作品充滿了精神力量。在這方面,首先觸覺到這一脈膊的又是畫家們--先是高更,然后是畢加索,他曾表示成熟的立體主義是從他對于"黑人"文化的熱衷時期過渡而來的。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貫穿著當代雕塑與考古學和人類學之間的交流。那些在這些學術領域造詣很深的學者常常是"現代派運動"作品的熱心觀眾。原始藝術品似乎在它們所導致的與現代藝術家作品的比較中日益成為正統的藝術,同時它們又將藝術的效力賦與現代作品。在這兩方面它都發生了影響。
在深受這類藝術品影響的雕塑家中,最熱衷的要算亨利·摩爾了,他早期創作的側臥形象就是直接取材于古代墨西哥人的chaemools(現在被普遍解釋為"上帝的信使"),還有阿爾貝托·賈科梅蒂。賈科梅蒂在其創作生涯的早期階段,與超現實主義運動有所聯系,那時他就對公元前二千年的基克拉迪斯石刻有濃厚的興趣。
原始藝術和古代藝術所產生的影響并不總像現代主義歷史學家一直認為的那樣具有進步的因素。為了改變從19世紀以及更前面的文藝復興時期繼承下來的雕塑形式,它的確是提供了一定的可供選擇的范圍,但是盡管杜尚作出了種種變受現狀的努力,雕塑卻仍被它限制在一個驚人的傳統的思維框架之中。一戰期間,有關雕塑自身本質方面的爭論很少--它的目標不在于所爭論的內容,只是表達這些問題的形式。
取代對原始文化發掘的一條明顯出路是在雕塑與機器之間建立一種關系,作為現代工業的象征,同時也作為整個西方社會一直在經歷的諸多變革的象征。一種機器美學的確是發展起來了,但是它與雕塑有關的部分卻很淺薄。在這一領域中,那些繼續根據構成主義傳統創作的雕塑家走在最前面。構成主義傳統自從在俄國被根除之后在西歐保存了下來。諾姆·加波和他兄弟安東尼·佩夫斯奈等雕塑家的構思很復雜,沒有直接模仿機器的形式,但在他們的作品中,尤其是在加波的作品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工業設計師設計的新形式的雛形。雕塑與機器之間的聯系由于使用新型材料而得到加強,比如塞璐珞和其他類型的塑料。"裝飾藝術運動(ArtDecomovemeut)中的次要藝術家們則樂于更加直接地運用機械形式,古斯塔夫·邁克羅斯就是一例。邁克羅斯作品的暗示使人既體會到機器形式又體會到非洲藝術形式,將兩個世界的最佳狀態結合于一體。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包浩斯是機器美學傳播的主要中心之一,培養了許多重要的建筑師和工業設計師,卻只產生了一位著名的雕塑家馬克斯·比爾,他的主要雕塑活動時期是在1945年之后。
有一項雕塑創新最早來源于手工工藝,而不是工業技術,但后來與后者結合在了一起,這就是鍛造和焊接金屬的應用。最早使用這一技術的藝術家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巴黎畫派的成員,他們具有西班牙血統,并且扎根于西班牙裝飾金屬的傳統工藝。帕布洛·加加羅率先邁出了第一步,他于1911年開始用薄鐵板和薄銅板制作面具,將它們錘擊、彎曲、切割,再裝配在一起。到了20年代,他的榜樣被他的同胞朱里奧·岡薩雷茲所繼承,后者來自巴塞羅那的一個金屬冶鍛工匠家庭,是一個不成功的畫家。岡薩雷茲經歷了一個很長時期的獨自思索和試驗,直到1927年他才下定決心完全投身于雕塑之中。1928年畢加索將岡薩雷茲招為助手,因為這時畢加索開始從事用焊條制作雕塑的實驗性工作,需要這種新方法的技術上的幫助。在畢加索的啟發下。岡薩雷茲很快從一個立體派傾向的人轉變過來,制作出像《博大的母性》(1930-1933年)這樣類型的作品)它們采用了三維繪圖般的開放形式。岡薩雷茲的工作具有關鍵的意義,他為許多藝術家提供了一個新的出發點,比如美國的戴維,史密斯·史密斯不像那些巴黎畫派的西班牙人,他來自于一個具有大工業背景而不是手工業的家庭,并且他已經于30年代制作了源于工業廢料的雕塑作品。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由機器零件組成,保留了對它們原型的暗示,而且往往不僅僅是暗示。超現實主義者擅長將不諧調的部分組合創造出新實體,它的主要感染力在于它所激發起來的聯想。在史密斯的手中,這一技巧獲得了新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畫廊是專為戰后時期的雕塑家而開設的,其中最偉大的雕塑家之一就是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