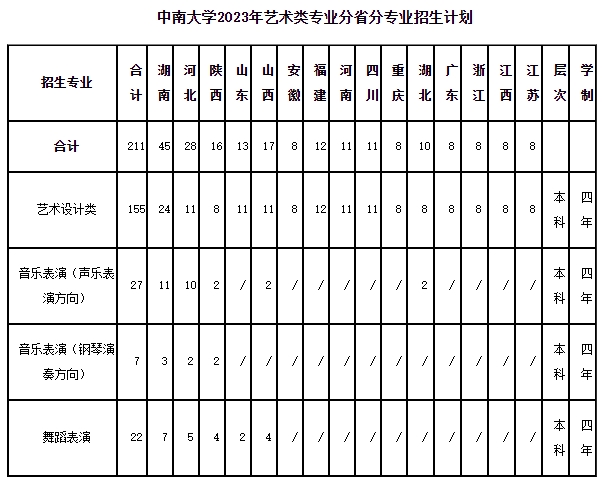漫話竹刻藝術(shù)(明清竹刻藝術(shù))
一
竹刻藝術(shù)的發(fā)端,
與中國其它傳統(tǒng)藝術(shù)一樣,
源自文人對自然的癡愛。
上古社會的遺址發(fā)掘中,
倘未發(fā)現(xiàn)有雕飾的竹器。
遺世較早有高度文飾的竹器,
是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彩漆竹勺,
勺柄以浮雕、透雕兩種技法刻有龍紋和編辮紋。
竹刻技藝至唐已是窮工殫巧,
神鬼不逮。
宋代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記述:唐德州刺史王倚家里有筆管一枝,
“刻《從軍行》一鋪,
人馬毛發(fā),
亭臺遠(yuǎn)水,
無不精絕。
”其畫跡若粉描,
必須在向明處才能辨別。
這件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竹刻藝術(shù)品,
據(jù)傳是用鼠牙雕成。
現(xiàn)藏日本正倉院的唐代雕竹尺八,
遍體紋飾用留青法淺雕仕女、樹木、花草、禽鳥諸物象,
與唐代金銀器鏤鏨及石刻淺雕,
同一意趣。
宋代的竹刻藝術(shù)又有進一步的發(fā)展。
《輟耕錄》記述了南宋紹興年間竹刻家詹成所制的一件鳥籠:“四面花板,
皆于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
纖悉俱備,
其細(xì)若縷,
而且玲瓏活動”。
詹成是見于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竹刻藝術(shù)家,
沒有作品傳世。
二
明代以降,
竹刻藝術(shù)最初由具有深湛藝術(shù)造詣文人奏刀,
“隨后或父子相傳,
或師徒接受,
或私下仿效,
習(xí)之者眾,
遂成專業(yè)。
”然而令竹刻藝術(shù)名傳天下的首推朱氏三子。
朱松鄰名鶴,
字子鳴,
號松鄰。
作為明代練水派竹刻的始祖,
平生所制有筆筒、香筒、杯諸器,
以及簪釵等首飾名重于世。
有詩贊:“玉人云髻堆鴉處,
斜插朱松鄰一枝。
”朱松鄰的作品遺世絕少,
現(xiàn)所流傳刻有朱松鄰款的竹器,
有專家考證,
以為皆是贗品。
唯有南京博物院藏的一只竹刻筆筒可視為真跡。
該筆筒以高浮雕的刻法,
雕老松兩株,
松下雙鶴,
仰俯相望。
款刻陰文,
行楷,
宗法晉唐。
1511年作。
但是,
此筆筒也曾引起置疑;“筆筒所刻老松的主干密布鱗皺癭節(jié),
松針刻若扇展,
層層疊落,
其旁又生一松,
虬枝紛橫,
蟠屈擰轉(zhuǎn),
有失挺拔。
仙鶴重于古拙,
矯健不足。
有專家評論,
此筆筒似過分渲染壽意,
以致構(gòu)圖欠精練。
如取朱之子小松、孫三松的作品比較,
此筆筒的技藝未免遜色。
”這一評價并未動搖其為真跡的定論,
朱為一文士,
繪事之余,
奏刀刻竹,
出自一片愛竹之心,
雖欲逼肖,
而求生趣達(dá)意則是作者主要的創(chuàng)作目的,
也就不慮是否肖似,
構(gòu)圖亦欠完整。
松鄰之子名纓,
字清父,
號小松,
居清鏡塘。
小松有乃父之風(fēng),
貌古神清,
工小篆及行草。
畫尤長于氣韻,
善仿王維諸名家。
小松“能世父業(yè),
深得巧思,
務(wù)求精詣,
故其技益臻妙絕”,
“刻竹木為古仙佛像,
鑒者比于吳道子所繪”。
小松性喜飲酒,
常與當(dāng)時畫家諸人游治,
又愛將小樹翦扎,
供盆盎賞玩。
當(dāng)時嘉定的竹刻和盆樹的藝術(shù),
由于小松的創(chuàng)作、推倡,
聲名遠(yuǎn)播。
小松的傳世作品,
有刻于萬歷年間的《歸去來辭圖》筆筒。
其代表作是現(xiàn)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劉院入天臺香筒,
在直徑僅37厘米的竹筒上,
刻有神仙洞府,
劉、院對弈,
刀法之工,
世無一可與其比高,
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幽邃縹緲的仙境,
令人棄履塵寰。
為明代竹刻藝術(shù)的典范。
朱小松的小兒子稚征,
號三松,
亦以竹刻出人天地。
三松不似其祖及父那般耿介孤絕,
而是具有隱逸文人的簡遠(yuǎn)恬淡。
這一性情,
使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情緒上更接近當(dāng)世的畫家吳偉、沈周,
繪筆之間給人一種平和的感覺,
非常安閑。
他善畫遠(yuǎn)山澹石,
叢竹枯木,
尤長畫驢。
作為一名平和的文人,
三松對功利的追求顯得十分的淡漠,
在進入商業(yè)化的明代,
他的作品透出一股清純之氣。
他除善刻筆筒、人物、秘閣、香筒外,
不斷地將自然界的各種生動形態(tài),
畢現(xiàn)于刀鍔之下。
如螃蟹、蟾蜍、殘花、夏荷等。
傳世精品有清宮舊藏,
現(xiàn)于臺北的窺簡圖筆筒。
“窺簡圖”出自《西廂記》,
筆筒上刻一高髻女子,
背屏風(fēng)而立,
雙手持一書卷,
傾神默讀,
另一女子潛出屏后,
蝶躞欲前,
指掩櫻唇,
側(cè)面窺視讀書簡之女。
二女一背一側(cè),
神意各異,
生于專情與顧盼之間。
亦藏于臺北的三松所刻的殘荷洗,
以竹根雕成,
半花、殘荷、小蟹,
狀寫入微。
朱氏三世刀筆并舉,
書畫兼融,
神話、歷史、童叟仕女、山水,
松竹梅、花卉禽鶴等,
一一皆達(dá)于竹、角、牙、木之上。
經(jīng)學(xué)者著寫詞章,
令當(dāng)世人競相學(xué)摹,
以為專業(yè),
由此形成了相傳百代的嘉定派。
嘉定派竹人在構(gòu)圖上顯示出了獨特的天賦,
常用立視或通景。
立視體雕刻,
講究層次,
“洼隆淺深可五六層”。
以浮雕為主,
兼融毛雕、淺刻、深刻、留青和透雕。
以使所刻景物“仙翁對弈辨毫發(fā),
美人徒倚何娉婷。
石壁岣巖入煙霧,
澗水松風(fēng)似可聽”。
通景雕刻,
一般用于在圓形器物上狀寫人物故事,
刻石屏分割景界,
人物景致徐徐展開,
人物中間刻松竹、夏荷、奇石、透窗、幾案等,
富有敘述性。
三
明代的嘉定盛行竹刻筆筒、臂擱、詩筒、棋盒,
不遠(yuǎn)的金陵卻流行竹刻扇骨。
當(dāng)世人稱“雕邊”。
明代摺扇是于永樂年間自朝鮮傳入。
至宣、統(tǒng)年間以雕扇鳴于時世的有李昭、馬勛、蔣三、蘇臺,
后有邵明若、李文甫和濮仲謙。
僅濮仲謙成大器,
創(chuàng)金陵派。
《太平府志》稱濮仲謙所制“一切犀玉髹竹皿器,
經(jīng)其手即古雅可愛,
一簪一盂,
視為至寶。
”濮仲謙的外貌與朱氏恰成相反,
其貌若無能。
“而巧奪天工焉。
其竹器一帚一刷,
竹寸耳,
勾勒數(shù)刀,
價以兩計。
然其所以自喜者,
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jié),
以不事刀斧為奇,
經(jīng)其手略刮磨之遂得重價。
”由此可見濮仲謙只以竹的天然形態(tài),
巧刃雕磨,
而顯神異。
濮仲謙率意奏刀,
自然成器,
真正達(dá)到了竹刻藝術(shù)化平凡為神奇。
人稱濮仲謙的竹刻直追漢代雄豪之風(fēng),
與漢石刻一脈相通。
后人宗濮仲謙為尊,
擴門戶漸成金陵一派。
有人評價濮仲謙的竹刻“淺率不耐尋味”。
濮仲謙的刻法與朱不同,
朱是深刻“洼隆淺深可五六層”,
濮是淺刻,
勾勒數(shù)刀。
兩人之所以風(fēng)格殊異,
是因起手所刻器物不同。
朱的竹刻起手刻筆筒厚重圓深,
深刻方能盡顯韻味,
濮氏操刀發(fā)軔于扇骨,
巧出淺鏤。
是故濮仲謙所代表的金陵派的竹刻,
為淺刻兼略施刀鑿。
明代以淺刻擅長的竹刻大家還有李文浦和張希黃,
李鐫花草,
玲瓏有致。
張刻竹取“留青法”。
所謂“留青法”是保留外皮的花紋,
刮去花紋以外的表皮,
露出淡黃色的竹肌作地。
刻后一二載,
表皮呈淡黃色,
竹肌由淡而深,
成深紅紫,
越久色澤差異越顯著,
“跡若粉描”,
古雅雋美。
張取“留青”為陽紋花紋,
“凡云氣、夕陽、炊煙,
皆就竹皮之色為之,
妙造自然,
不類刻畫,
亦奇玩也。
”張被后來的仿效者尊為“浙派”的開山之人。
朱的高浮雕或圓雕、濮的淺刻兼略施刀鑿,
張的淺刻為明代刻竹的三大風(fēng)格,
傳于后世,
并用于牙、角、木等不同材質(zhì)。
四
清初失意的文人,
求仕不得賦閑家中。
而在異族的扼抑下,
閑居家中的文人既沒有宋人那份平靜的心境,
又無法象元人一般隱逸山林。
當(dāng)不成隱士的文人,
只得以繪馬遠(yuǎn)、夏圭及“元四家”的山水,
從表達(dá)自己與自然的親和中,
標(biāo)榜自己的隱逸精神。
復(fù)古成為清初藝術(shù)的主題。
竹刻藝術(shù)家在復(fù)古的情緒中,
表現(xiàn)出更加安靜的心態(tài),
使得竹刻技藝愈加精湛。
突出的表現(xiàn)是作品的造型較之明代豐富了,
多見有酒瓢、詩筒、筆筒、香筒、筆架、鎮(zhèn)尺、臂擱、人物、仙佛、草蟲、朝殊盒、翎筒、竹章、棋盒、竹筷、墨床、籌碼等。
清初至乾隆的150年間,
名冠天下的竹刻大家有吳之璠、封錫祿、周顥、潘西鳳四人。
嘉定竹刻自朱氏創(chuàng)始,
承其技法者,
頗不乏人,
名家有沈兼、王易、周乃始、殷介持、陳雪笠、劉韓抒和吳之璠。
其中得朱氏真髓的為沈兼、王易、吳之番。
沈兼字兩之,
父親曾從三松學(xué)竹刻。
沈耳濡目染,
盡心參摹,
得真?zhèn)鳌?
沈兼的竹刻少有傳世,
有人曾藏沈兼一淺刻蘇髯赤壁圖筆筒,
上刻扁舟一葉,
泛于煙水,
云際明月間,
赤壁危崖摩天,
石間葦荻叢生,
夜風(fēng)中婆娑有聲。
此器為練水典范之作。
王易字又白,
工書畫而兼善音律,
雕鏤雜技更極人巧。
其所刻竹秘閣淺雕垂柳拂絲,
柴門短墻,
隱于煙霞嵐風(fēng)間,
長堤擔(dān)橋,
一舟穿渡,
水波蕩鱗,
捧于掌中有覺晚風(fēng)拂面。
清初嘉定一派高手,
或作人物山水,
或行草隸楷,
皆精妙無可喻。
然而,
對后世刻藝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是吳之璠。
吳之璠字魯珍,
號東海道人。
他受清初畫壇的復(fù)古影響,
竹刻“大抵花鳥規(guī)摹徐熙,
寫意人物山水有馬、夏之間。
”吳之璠畫道以南宗為正法,
刻竹則多崇北宗,
“以刀代筆,
簡老樸茂,
逸趣橫生一派,
易易得神。
”除立體圓雕,
吳善浮雕,
刀法有兩種。
一是深刻作高浮雕,
即朱氏刻法,
深淺多層,
高凸處近乎圓雕,
低深處可用透雕;另一是淺浮雕,
此乃吳自創(chuàng)。
吳深諳畫理,
巧用景物的遮掩壓疊,
分生出遠(yuǎn)近、層次,
在浮雕有限的高度上,
產(chǎn)生透視的深度,
潤澤的竹肌上有精鏤細(xì)琢的圖文,
它與樸質(zhì)無的素地,
相映生趣。
此種刻法同朱氏于器物周身刻滿景物相比,
更加雅逸。
有人譽吳的淺浮雕有北魏碑味,
取龍門之法。
尤其他的“薄地陽文”刀法,
工絕無匹,
后世談起吳的竹刻,
薄地陽文成了其竹藝的代詞,
為人推重。
吳的創(chuàng)新豐富了中國竹刻技藝,
他的這種敏而不倦的精神,
也使他為后世留下數(shù)量可觀的竹刻絕品。
嘉定竹刻逐漸形成兩種刻風(fēng),
一是刻筆筒,
以竹筒的周圓為畫面,
如筆筒、酒杯、香筒諸器。
一是雕老竹根,
隨其高低、曲折、淺深,
刻人物山水、花卉果蔬等,
也就是現(xiàn)代的立體雕刻,
清時稱“陽文”,
嘉定“陽文”雕刻至康熙朝,
封錫祿、封錫爵、封錫璋兄弟一門大著于世。
封錫祿字義侯,
擅圓雕竹根,
“其摹擬梵僧佛像,
奇蹤異狀,
詭怪離奇,
見者毛發(fā)竦立,
至若采藥仙翁、天女散花,
則軒軒霞舉,
超然的出法之想。
”其“或雕仕女狀,
或鏤神鬼形,
奔出脛疑動,
拿攫腕疑擎。
”“寫愁如困約,
象喜如豐亨”。
后人評價嘉定的竹根人物雕刻是“盛于封氏,
而精于義侯”,
即封氏兄弟將竹根藝術(shù)推向頂峰。
清初江南書房陳設(shè)的風(fēng)氣傳入清宮,
竹雕等文玩開始作為清供,
陳擺在皇帝的書案上。
封氏一門因竹刻技藝獨絕,
世人“智勇莫能爭”,
養(yǎng)心殿總管年希堯命封氏兄弟入京,
藝值養(yǎng)心殿造辦處。
封氏三兄弟的竹刻作品,
傳世無幾。
五
清乾隆以前,
無論嘉定還是金陵,
精擅竹藝的代有人出。
到了乾隆,
那種精工細(xì)琢的刻法,
人們覺得雖然心機處處,
神肖逼真,
卻少乏生氣。
這種生氣的缺乏并不僅僅指作品本身,
包括竹刻家的心靈和手法的板滯。
自朱之后的竹刻大師多不再是抒發(fā)雅興,
消遣游戲的文人,
變成了終生為藝師。
進入專業(yè)化后,
竹刻家們也許出于一種對自我職業(yè)的天然敬意,
除少數(shù)人外,
承襲摹擬前代,
成了主要的創(chuàng)作,
以使門派名聲不墮。
自我情感在一種不自覺的繼承和求精中,
無法直抒。
那精湛的雕刻,
也就少了一份靈性。
至乾隆,
“四王”院派雖風(fēng)頭尚勁,
在野文人的創(chuàng)作仍是畫壇主流,
由“揚州八怪”開啟的創(chuàng)新之風(fēng),
直接影響了江南竹刻藝術(shù)的變革。
嘉定的美髯公周顥世居嘉定城南,
磊落不羈,
有竹林七賢之風(fēng)骨。
他讀書而不應(yīng)科舉,
曾問業(yè)于王石谷,
得其指授,
后師法南宗。
周喜畫竹,
風(fēng)枝雨葉,
冷冷然如劍摩長空。
自朱以來,
刻竹者皆竹人兼畫家,
周顥乃是畫師而兼竹刻;周之前的竹刻家山水人物師法北宗,
周獨出手眼,
合南北為一體,
行刀如其人,
以無厚入有間,
爽爽有力,
畫手所不得到到能以寸鐵寫之。
周作山水樹石叢竹,
“以陰刻為主,
輪廓皴擦,
一刀剜出,
闊狹淺深,
長短斜整,
無不如意。
樹木枝干,
以印鋒一剔而就,
有如屈鐵”。
所謂“用刀如筆,
不假稿本,
自成丘壑。
”
周顥傳世代表作有“溪山漁隱”、“仿黃鶴山樵山水”、“松壑云泉”等三件筆筒。
他的竹刻風(fēng)格,
后人競相爭摹,
以至清代后期的竹刻家們多“不求刀痕鑿跡之精工,
但矜筆情墨趣之近似。
于是精鏤細(xì)琢之制日少,
荒率簡略之作日多。
”
乾嘉以后,
文人多喜愛篆刻,
甚至親自奏刀。
因此竹刻家中不乏文人雅士。
潘西鳳號老桐,
操刀刻竹,
為了從因頓的生活中解脫出來。
因此,
他以文人的雅逸審美,
摒棄雕飾,
用淺刻手法求天然渾成之妙。
所刻的臂擱,
全無雕飾,
用畸形卷竹裁截,
竹上蟲蝕斑痕宛宛可見,
令人疑其未經(jīng)人手。
其雕筆筒,
取土下數(shù)節(jié)略加裁刻,
給人一種天然趣成的圓熟。
由于受世風(fēng)影響,
飽學(xué)之士的老桐,
刀下篆隸,
得秦漢遺法,
淳古渾勁,
呈刻于竹上,
一派高古絕俗之氣。
鄭板橋曾把老桐的刻竹印,
鈐入“四鳳樓印譜”。
吳之璠的薄地陽文,
封氏兄弟的圓雕,
周顥的運刀如筆,
以及淵西鳳的隨意刮磨得自然之趣的技藝,
在清代三百年間冠絕天下,
無人出其右。
四人中僅潘西鳳因居揚州,
曾被鄭板橋譽稱“濮陽仲謙以后一人”,
世人都視他為金陵派。
六
吳、封、周、潘等四家的竹刻,
將中國的刻竹藝術(shù)推向鼎盛,
這一時期前后長達(dá)近二百年。
清代中期以后的竹刻家雖多有記載,
而竹刻作品同中國其它傳統(tǒng)藝術(shù)品一樣,
無論制作的工藝,
還是設(shè)計的構(gòu)思,
都象這個國家,
漸入末途。
至清末以來的連年戰(zhàn)爭使文人最終放棄了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那份安逸的心境。
竹刻家們與末代帝王一般,
將主要的精力用于沿襲,
“自具面目,
堪稱大家的實罕其人。
”
前代藝術(shù)家皆是工書善畫的文人,
使得竹刻的山水花鳥、神仙佛鬼、高人逸士、娉婷仕女等形態(tài),
逼真?zhèn)魃瘛?
清中晚期吳門、嘉慶兩地的竹人以色勒法作書畫雕刻雖自具風(fēng)格,
立戶開派,
但是,
竹刻家多不是文人出身,
書畫一道僅知臨摹,
所以已不能自畫自刻,
只得求畫家設(shè)計打稿。
書畫與刻竹成分家之勢后,
竹人漸漸淪落成有如一般作坊內(nèi)的刻工。
由于文人在竹子上作稿只能落墨一次,
所以,
清末以來的竹器常是淺刻,
或陽文或陰文,
鉤勒名人書畫、金石文字的竹刻,
風(fēng)靡江浙。
然而,
一些鳴世竹人,
只能以鐫刻名家書畫見長,
不能自創(chuàng)畫稿。
在這一衰落中雖也有秀韻超逸之作產(chǎn)生,
但是,
竹刻家耽于競巧斗異,
纖弱矯情,
已無嘉定派的天然渾厚;綽約多姿,
也無金陵派的淳古妙雅。
至同光年間,
連圓雕、高浮雕、透雕等竹器也愈見稀少,
進入民國,
竹刻諸法幾近失傳。
市上流行的竹刻器多為臂擱、扇骨、圓雕竹器精品十分罕見。
清末,
文人在政治的極端黑暗中,
終于失去了美化的生活追求。
盡管,
無數(shù)優(yōu)秀的工匠力圖拘回頹勢,
卻由于不擁有產(chǎn)生這門藝術(shù)的濃厚文化,
以至想要光大竹刻藝術(shù)的理想,
最終還是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