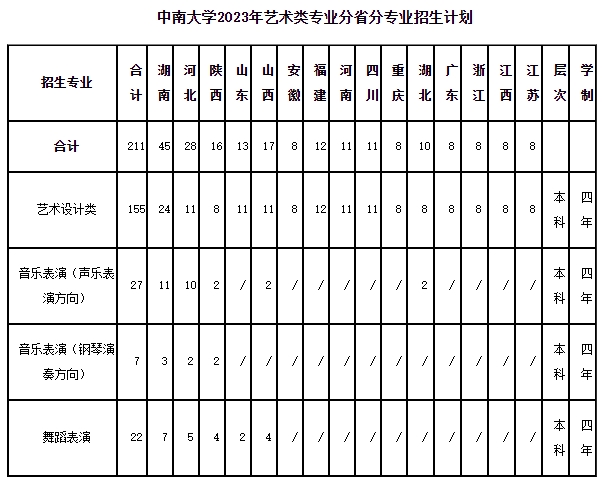論色調3(論色調在影視制作中的)
法國的畫家米勒,在他的作品《晚鐘》里,用朦朧的暖色調,描寫了兩個貧苦農民在一天的辛勤勞動之后,站在充滿空氣感的茫茫暮色中應和著遠方教堂的鐘聲,向那并不存在的上帝祈禱幸福。他們虔誠但愚昧,樸實卻無知,善良但貧窮,勤勞卻很少收獲,這是十九世紀法國貧苦的但未覺悟的農民感情的真實寫照,也是米勒的自我寫照。畫面上的暖灰色調處理得極為精細而充滿感情:朦朧的空氣感,似乎散發著泥上的香氣,大地也在朦朧中展向與大氣相接的遙遠的天邊,我們看到的是普通的、人物,普通的環境,普通的色調。感受到的卻是誠摯、樸實的感情。
我們既要研究生活,也要研究前輩畫家的經驗。看看前人是怎樣運用色調語言來表達感情的。但是色調與情緒的聯系是極其微妙的、復雜的。總之是千變萬化的,決不能把前人的經驗當作包治百病的妙方。更不能憑主觀的思維與推理,定出一些清規戒律。像"四人幫"霸占畫壇時那樣:灰色調、暗色調、冷色調被劃為禁區,只能用以表現舊社會。而社會主義的今天,就只能用暖色調、亮色調,或者不顧色調的統一性,把工、農、兵和領袖畫得面色朱紅,或者虛情假意地到處用所謂紅亮調子。這種形而上學影響下產生的作品,不但毒害了觀眾的眼睛,也奴役了畫家的感情,只能導致藝術的沒落和死亡。
色調與人們情緒的聯系源于生活,畫家也只有在生活中挖掘探索新的聯系,才能豐富色調的表現力。
在李煥民的套色木刻《初踏黃金路》中,明亮暖黃的色調是與藏民豐收的喜悅情緒凝結在一起的,列維坦的《金色的秋天》的暖黃色調雖然也顯示出富饒、寧靜的美麗,但卻帶有幾分傷感情緒。而在列賓的《伏爾加纖夫》中,明亮的暖黃色調絲毫不能使人感到喜悅和愉快。相反,它表現在毒烈的陽光下,灼熱、焦燥得難于忍受的痛苦情緒,從而更深刻地揭示出這群被剝削、被驅使的纖夫的奴隸般的處境。
這些同是以暖色調為基調,而畫面所體現的情緒和感情卻是那樣不同。說明色調決不是能借以大批復制的模具,而是表現生活與畫家情感的千變萬化的藝術手段。
色調、感情、意境
我們研究色調與情緒的聯系,是為了運用色調抒發感情。感情是藝術的靈魂,沒有感情,藝術就沒有生命。
人都是有感情的。但并非人人都能成為藝術家。有情無意,不能形成藝術品。"意"是"情"的形象化的集中表現,藝術家不同于一般人就是因為他善于使感情轉化為"意",并通過藝術語言創作出藝術品。中國畫論中講"立意",就是"情"的形象轉化。"意"又是藝術品在作者頭腦中的胚胎,也就是構思。構思醞釀成熟才能做到"胸有成竹"、"意在筆先"。
詩、文的立意,是通過語言。繪畫的立意,要通過形象。而油畫的立意,要通過色彩的形象,通過色調。色調的分寸恰當,"意"就傳達得明確,"情"也體現得充分,反之,色調與"意"相矛盾,"情"也無從表達,俄羅斯畫家薩文斯基的油畫《遷徙》,本意是想表現遷徙者在途中死亡的悲劇場面。但作者采用的是明朗、柔和的暖色調,初看好像是遷徙者在休息、睡覺。從整個畫面看來感覺不到悲哀的情緒。相反畫中色調似乎是在奏著輕松明快的曲調,效果適得其反。
所以油畫立意不能離開色調,確定色調更不能脫離立意,色調應服從于"意"。但服從"意"不能理解為消極的適應或說明,俄羅斯風景畫家希施金的某些描寫陽光下森林的風景畫,雖然也有色調,但在那些畫中色調只是停留在說明光照時間與環境上。雖然準確逼真,也僅只是準確逼真而已,畫面感受不到作者的感情與色調之間的聯系,色調的情感不明確。他只作到了以色寫實,沒能做到以色抒情,畫面缺乏意境。所以色調服從于景,只能達到寫實,色調與"意"的高度統一,才能在畫中表現意境。
意境是通過情景交融的藝術形象以達到詩意的境界,我國詩人和畫家歷來最講求意境,提倡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認為詩是無形的畫,畫是有形的詩,油畫雖然是外來畫種,但是完全應該而且能夠做到通過色調表現詩意的境界。
《烏克蘭的傍晚》,正是通過景物的色調,抒發了作者對烏克蘭山村深深的愛。那是夕陽銜山的一剎那。夕陽的余暉依戀著白色的茅舍,茅舍依戀著夕陽的余暉。在這轉瞬即逝的一剎那,色調凝聚著作者的深情。使這幅畫象一首寧靜、優美、樸素的田園詩篇。
列維坦的《弗拉基米爾路》則表現了另一種意境:陰云滿天,衰草遍地,茫茫的荒野上幾乎沒有人煙。一條坎坷不平的路伸向遙遠的天邊--這是革命者流放之路,一切都籠罩在滿目凄然的情緒里。不由得使人記起,"愁云慘淡萬里凝"的詩句。作者的感情通過畫面的灰色調,深深地感染著觀眾。觀眾的心也隨著作者的"意"向著遙遠的天邊,對那些被流放的革命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多少觀眾為這張畫深深地感動著,多少觀眾在離開畫面時仍帶著沉重的心情。意境把觀眾帶入畫中,又超出了畫外,給觀眾提供了廣闊的想象余地。
中國古人論詩,指出,"詩言志"。蘇東坡認為"作詩即此詩,必定非詩人"。唐人白居易的名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表面上似乎描寫了自然現象,但其中卻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它展示了一種斗爭的韌性,它讓人們看到好與壞,順境和逆境……相互轉化的規律性,它使革命者處于革命低潮時堅信勝利到來的必然,它使遭受不公允待遇的人能看見希望。因而堅持著、斗爭著、等待著。同樣一幅優秀的畫,也不應是"作畫即此畫",而應有畫外意。應使觀者有所感觸,有所激動,有所聯想,有所啟示。才能使觀者玩味無窮,百看不厭。這正是作品深刻的思想性與高度的藝術性相結合、相統一的結果。這種作品才能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弗拉基米爾路》正是許多這類優秀作品中的一幅,它的色調對畫面情緒、意境起了非凡的作用。
通過色調表現意境是油畫的特長,但在表現意境時色調不是孤立起作用的。它總是依附于具體形象而發揮威力的,離開了造型形象,孤立的色調就不可理解了。試想《弗拉基米爾路》如果沒有那條道路,沒有那樣的荒野,那樣的天空,只是幾團顏色,幾組色塊,它怎么能深深地打動觀眾呢?又怎能發人聯想?所以我們也不能把色調的作用夸大到不適當的地位。
通過色調抒情和表現意境,是油畫家應具備的高度技巧。當然技巧不是目的,不能為技巧而技巧。運用色調的技巧,是為了更好地抒情寫意,集中地突出形象、意境。但我們也不是"唯情論",只要有情就一切都好。歷史上一切偉大的藝術家之所以偉大,不僅在于他有感情,也不僅在于他有化情為意的高度技巧。雖然,這些全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所表達的感情是進步的、高尚的、能代表人民的,而且是真摯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畫家達·芬奇,把他真摯的感情傾注在肖像畫《蒙娜麗莎》的描繪上。這張端莊、健康、嫻靜、溫柔、自信的婦女形象是階級的肖像,是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理想美的化身。是對中世紀宣揚病態美的挑戰。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島的屠殺》是為被侵略、被壓迫和被屠殺的希臘人民而寫的控訴書,也是為一切被侵略和被壓迫的人民伸張正義而作。列維坦為反對沙皇而遭鎮壓的革命者唱著低沉而激奮的挽歌,就是那幅感人的《弗拉基米爾路》。這些作品在當時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崇高的感情,是那些脫離人民、逃避現實的頹廢、瘋狂的沒落階級的感情所無法比擬的。這確實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也確實來不得半點虛飾和偽裝。"文如其人",畫亦如此。"四人幫"的反革命命靈魂不論它打出多么漂亮的革命的旗幟,也掩蓋不了他們那種粉飾太平,矯揉造作的假革命藝術實質。還是魯迅先生說得中肯:"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
我們的時代里,一切技巧,包括運用色調的技巧,只有表現我們偉大時代最先進的、崇高的、真摯的無產階級感情時,才能發揮它最燦爛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