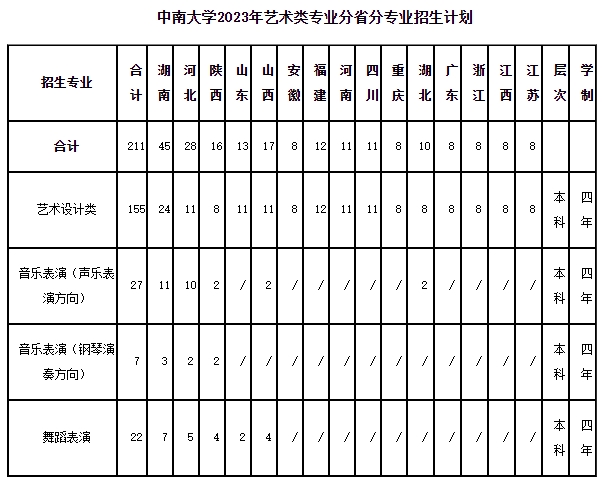中國畫的意義世界
一
錢鐘書曾經指出,“中國傳統文藝批評對詩和畫有不同的標準;評畫時賞識王世禎所謂‘虛’以及相聯系的風格,而評詩時卻賞識‘實’以及相聯系的風格。” 究竟什么是“實”什么是“虛”?為什么畫以“虛”勝而詩卻以“實”勝?對于這些問題,錢鐘書沒有深究,也許在他眼里,這是中國傳統文藝批評中再明白不過的道理了。但正是在這些表面上明白不過的道理中,卻潛伏著矛盾和困惑,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畫都比詩“實”,詩都比畫“虛”。詩言志,畫圖形; “形”在外是“實”,“志”在內是“虛”。因此,黑格爾說詩歌比繪畫更高級,更具有精神性,也更“虛”。當然,我們也可以用黑格爾式的辯證法來解釋這里的矛盾:本身是“虛”的詩相反要追求“實”的境界,本身是“實”的畫相反要追求“虛”的境界。但這種辯證法式的解釋,難免給人一種簡單草率之嫌。
徐復觀的一段文字似乎可以看作這里的“虛”與“實”的注釋。他說:“我國文學源于五經。這是與政治、社會、人生,密切結合的帶有實用性很強的大傳統。因此,莊學思想,在文學上雖曾落實于山水田園之上,但依然只能成為文學的一支流;而文學中的山水田園,依然會帶有濃厚地人文氣息。這對莊學而言,還超越得不純不凈。莊學的純凈之姿,只能在以山水為主的自然畫中呈現。” 按照徐復觀的解釋,詩文之所以是“實”,因為它跟政治、社會、人生密切相關,與實用性密切相關;繪畫之所以是“虛”,因為它超越了各種人事的實用性的考慮,只是以純凈的自然山水為對象。套用西方美學的術語,詩文之所以是“實”,因為它是“有利害”考慮的,我們與事物之間的“心理距離”(psychical distance)太近;繪畫之所以是“虛”,因為它超越了利害考慮,是無利害的(disinterested),我們與事物之間保持著適當的“心理距離”。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詩歌更容易接近利害考慮而繪畫卻更容易超越利害考慮?徐復觀對此沒有進一步的說明。我想除了受到傳統的影響之外,就像徐復觀所主張的那樣,中國詩文之所以不能完全落實藝術精神是因其源于五經,受到注重實用性的儒家傳統的影響,媒介的不同也是一個主要原因。中國詩文不僅源于五經,而且在其發展演變中還很難擺脫五經的影響,這是由詩文使用的語言媒介的本質特征決定的。語言,不管多么詩化的語言,總有概念化的傾向,從而為闡釋者作道德文章的引申提供了可能。而繪畫,特別是文人山水畫,由于其運用的材料主要是筆墨,是一些不能被概念化的東西,所以比起詩文來,更容易超越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局限,而接近由莊學發展起來的自然的藝術精神。
詩文與繪畫之間的媒介不同,不僅可以用來進一步說明為什么中國詩文尚“實”,而中國繪畫崇“虛”,而且可以以此為契機來闡釋中國畫的意義世界。
二
如果中國詩文因為擺脫不了概念理解因而顯得很“實”的話,那么中國繪畫的“虛”就體現在它呈現了我們在概念之前或之下對事物的理解。如果我們將經由概念的理解稱之為理解(understanding)或概念理解的話,那么在概念之前或之下的理解就是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或前概念理解;如果我們在理解中獲得的是關于事物的知識(knowledge)的話,那么在前理解中獲得的是關于事物的前知識(foreknowledge);如果我們將在概念理解的知識中顯現的世界稱之為真實(real)世界的話,那么在前概念理解的前知識中顯現的世界就是前真實(pre-real)世界。前真實世界是一個比真實世界更本真、更源初的世界。
那么,究竟什么是前理解?什么是事物的前知識?什么是前真實世界?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跟與此相應的理解、知識和真實等對照起來說明。概念是一類事物所共有的本質特征,比如不管現實世界中的桌子多么千差萬別,桌子的概念始終保持同一。概念理解,就是將不同的桌子納入同一個桌子概念之下的理解,從而獲得關于桌子的穩定的、普遍有效的知識。根據認識論的一般看法,只有掌握了桌子的概念和知識,我們才把握了桌子的本質,洞察了桌子的真相。但桌子的概念并不是桌子。沒有一張桌子能夠完全符合桌子的概念,就像沒有任何一個實際的正方形像正方形的概念所要求的那樣方。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概念來理解周圍事物,周圍事物總是顯現為相對穩定和普遍有效的知識。但事物在概念理解中顯現的穩定的知識樣態,并不是事物的本真樣態,并不是事物本身。也就是說,我們平時信以為真的事物其實并不真實。我們的概念理解至少從兩個方面對事物進行了歪曲。首先是回憶再現的歪曲,其次是概念再現的歪曲。我們對事物的概念理解總是對已經在感知中出現過的事物的理解,如果說在感知中出現的事物是事物第一次與我們照面的話,那么在概念理解中出現的事物就是事物第二次與我們照面,是對第一次與我們照面的那個事物的回憶。這就是感知只能感知在場的事物而概念理解卻可以理解不在場的事物的原因。但借助回憶顯現的事物總不是事物本身,至少它削弱了來自事物的存在意義上的沖擊力,我們感受不到事物的壓力,或者說,事物不再是野性的事物,不再是體現必然性的事物,它已經被改造或馴化得服從我們的想像以便我們可以用概念來把握它了。這是概念理解對事物的第一次歪曲。第二次歪曲是讓事物在概念中出現。概念理解總是借助概念進行的,任何概念都只能描述事物的一般特征,在概念理解中出現的事物也總是顯現出符合一般特征的特征,它自身的豐富性和生動性被剪裁掉了。從這種意義上說,概念理解是對事物的強暴。
中國畫家并不描繪那個在概念理解中再現的貌似真實而其實不真的真實世界,相反他們要捕捉那個在前概念理解中呈現的貌似不真而其實本真的前真實世界。中國畫的意義世界就是在概念理解之前或之下的那個貌似不真而其實本真的前真實世界。
三
現在的問題是:所謂概念之前或之下的前理解就是一種怎樣的理解?存在這樣一種能夠通達事物本真存在或事物本身的理解嗎?從中國哲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前理解是肯定存在的,借用莊子庖丁解牛的寓言中的表達方式,前理解是“神遇”而不是“目視”,或者更一般地說是“以道觀之”。究竟什么是“神遇”或“以道觀之”?清代畫家鄒一桂《小山畫譜》中有段記載能夠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
宋曾云巢無疑,工畫草蟲,年愈邁愈精。或問其何傳,無疑笑曰:“此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叢間觀之,于是斯得其天。方其落筆之時,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我們從這個故事中可以區分兩種理解草蟲的方式:一種是對著草蟲時對草蟲的理解,一種是與草蟲融為一體時對草蟲的理解。我們對著草蟲時對草蟲的理解總不能擺脫草蟲概念的幕帳,總是用對草蟲的一般的穩定的知識來掩蓋草蟲本身。與草蟲融為一體時對草蟲的理解沒有草蟲概念的中介,或者說突破了草蟲概念的硬殼,這就是所謂的概念之前或之下的前理解,在這種前理解中,草蟲能夠顯現它的本真樣態(即所謂“斯得其天”)。
當代許多西方哲學家都否定有這種能夠顯現事物本身的前理解。比如,根據尼采的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根本不可能存在事物本身,所有的事物都是在語言解釋中構成的,不存在獨立于解釋之外的事物。這種主張也被稱之為普遍的解釋學立場。如果連事物本身都不存在,哪來的對事物本身的洞見?當代分析哲學家將那種事物可以離開解釋而存在的主張,稱之為“被給予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given)。分析哲學要破除的就是這種神話。不過,另一些哲學家主張,即使不存在離開解釋而存在的事物,但至少可以區分兩種不同的解釋,在其中的一種解釋中我們可以更接近事物本身。比如,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現象學考慮的核心問題就是那種在概念理解之下的身體感知的問題。我們的身體感官(bodily sense-organs)具有一種在思想、意識、心靈之下的感知能力,總之,具有一種在人之下(sub-personal perceptions)的感知能力。這種感知在我們在世界中存在時就已經發生了。我們關于世界的概念理解,事實上只不過是對這種已經發生的身體感知的回憶而已。再如,以發現默識知識或默識認識聞名于世的博蘭尼(Michael Polanyi)也表達了與梅洛-龐蒂類似的思想。在博蘭尼看來,我們對事物的意識可以區分為集中意識(focal awareness)和輔助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由心靈發出的集中意識是“對”(to)對象的意識,由身體發出的輔助意識是“從”(from)對象和身體自身的意識。因為在后一種情況下,對象已經變成了身體的一部分,從對象的意識實際上就是從身體的意識,也可以稱之為“寓居”(indwelling)或“內化”(interiorization)的意識。這種輔助意識所得到是事物的存在性意義(existential meaning),是非名言知識(inarticulate knowledge);與之相對,集中意識所得到的是指示性或表象性意義(denotative, representative meaning),是名言知識(articulate knowledge)。所謂名言知識就是概念理解所獲得的知識,所謂非名言知識就是前概念理解所獲得的意義或意蘊。
無論是梅洛-龐蒂的身體感知還是博蘭尼的默識認識,它們都指一種在概念理解之下或之前的理解。如果說概念理解主要是由我們的意識作出的,那么前概念理解主要是由我們的身體作出的。由此,我們可以總起來說,所謂前概念理解,就是我們與事物融為一體時對事物的內在領會。
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從鄒一桂所講的那個故事中,我們還可以發現,所謂前概念理解并不是指人在沒有掌握概念之前的理解,而是指有了概念理解的人在超越或還原概念理解之后的理解。這一點可以很好地反駁分析哲學的“被給予神話”的指控,同時也可以很好地避免將前概念理解等同為概念理解尚未發育完善的原始人或嬰兒的理解這種普遍的誤解。
四
如果說在概念理解中顯現的事物是穩定的“實在”,那么在前概念理解中的事物又是什么樣子呢?由于前概念理解很容易為概念理解所遮蔽,人們就將透過概念理解顯現的穩定的事物“實在”當作事物本身,但我們已經指明它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對事物的雙重歪曲。什么是事物沒有經過概念理解歪曲的樣子?這是一個非常有欺騙性的問題,因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容易陷入對事物的概念描述之中。不過,我們至少可以說,在概念理解歪曲之前的事物是“虛”的。這里的“虛”并不是它不存在,也不是說它虛幻不真。那么“虛”究竟指的是什么?
“虛”首先是虛掉事物穩定的實在性,一旦消解了事物穩定的實在性之后,我們就不會固執地以為事物是一成不變的,或者只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是真的事物。在前概念理解中顯現的事物由于與理解者的存在緊密相關,而理解者的存在又是有時間性的,或者說是在時間中展開的,在時間中展開的存在是有變化的,因此在前理解中顯現的事物總是活潑潑的、幻化生成的,但這并不等于它們是虛幻不真的。這種變化而真實的東西是如何可能呢?因為我們一般將真理解為確定不移的,沒有穩定性的事物我們根本就無法辨認它的身份,從而無法斷定我們關于它的認識的真假。不過,我們可以設想事物在時間之流中是變動不居的,而事物在時間之流中的每個時間點上是確定不移的,這樣我們至少可以說事物在每個時間點上都是千真萬確的,它們之間的真實性是不可比較、不可分級的。這就是我所說的“剎那真”的觀念。概念理解追求的是事物在時間流中的恒定性,前概念理解追求的是事物在時間點上的恒定性。在概念理解中的同一個事物,在前概念理解中可以千姿百態。事物的這些千姿百態都是同樣地真實,甚至可以更極端地將同一個事物的千姿百態看作千姿百態的不同事物。我們可以進一步將概念理解意義上的真稱之為“衍生真”,將前概念理解意義上的真稱之為“原生真”。“衍生真”之間的真實性是可以比較、可以分級的,“原生真”之間的真實性是不可比較、不可分級的。比如,今天對月亮的科學認識(概念理解中的“衍生真”)顯然比先秦時期更準確,但不能因此說今天人們對月亮的感受(前概念理解中的“原生真”)比先秦時期更真實。我們不僅不可以比較今人和古人在前理解中所把握的事物的真實程度,也不可以比較同一時代的自我與他人在前理解中所把握的事物的真實程度,甚至不可比較同一個自我在不同時間點上在前理解中所把握的事物的真實程度。在我的前理解中剎那現起的月亮可以不同于在你的前理解中剎那現起的月亮,但這并不意味著你我當中只有一人的前理解是真實的;在我此時的前理解中剎那現起的月亮可以不同于在我彼時的前理解中剎那現起的月亮,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于彼此不同時間點中的前理解只有一種是真實的。總之,事物的原生真實樣態可以是多種多樣,我把這種主張稱之為存有性多元論或在場性多元論(pluralism of presence)。
但我們并沒有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相反,這里有一種絕對性,一種必然性,一種對必然的真實感受的絕對服從。只要我們設身處地地感受,只要我們像人一樣地去感受,就能夠感受到事物的多種多樣的原初真實,感覺到它們都是同樣地真的。這種同樣的真的感受,不是來源于這些原初的真都是一樣,而是因為它們都是同樣的不一樣;它們都觸及到了自己的存在的根底,但在各自的根底上卻表現得千差萬別。相反,人們在概念理解層次上的認識盡管被證明是絕對真實的,但卻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被牛頓證明是錯誤的,牛頓的物理學被愛因斯坦證明是錯誤的,愛因斯坦的物理學也一定會被后來者證明是錯誤的。但沒有人去證明荷馬是錯誤的。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沒有人去讀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卻有人去讀荷馬史詩的原因。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造成事物在前理解中顯現的前真實樣態的差異性,事實上是理解者的風格的顯現。所謂風格,按照杜夫海納的理解,在根本上是一種情感特質。每個人給人不同的風格感覺或印象,源于每個人的不同的情感特質。這種不同的情感特質會給前理解中顯現的事物定下不同的情感基調,從而使事物體現出不同的風格。就藝術欣賞而言,任何藝術作品都有它的情感基調或風格,必須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調或風格才能準確地理解藝術作品。作品的情感基調與作者的情感氣質類似,因此我們可以用“歡快”來說莫扎特的音樂和莫扎特本人。這就表明,在莫扎特和莫扎特的音樂之間有一種內在的關聯,這種關聯不僅是情感性的,而且是先驗的。“歡快”這個先驗的情感范疇決定了莫扎特成為莫扎特,決定了莫扎特的音樂成為莫扎特的音樂。同時,我們只有通過“歡快”這個情感范疇才能進入莫扎特及其音樂的審美世界。
由于在前理解中顯現的世界是藝術家或感知者的情感特質或風格的顯現,因此可以說在前理解中顯現的世界是具有個人色彩的世界,甚至可以說是非常主觀的世界。但是,這里的主觀不能理解為主觀偏見,而應該理解為有差異的個體的真實存在樣態。我將這種主觀理解為一種“無主觀性的主觀心靈”。總是,中國畫表現的那個前真實世界,是一個比主觀主觀、比客觀更客觀的世界,是那個在主客體尚未分裂之前的原初世界。
五
讓我提出一個大膽的主張:中國畫對前真實世界的揭示,可以讓業已終結的藝術重獲新生。為了闡明這個主張,讓我簡單介紹所謂的藝術終結論的主張。
“藝術終結”(end of art)是黑格爾(G. W. F. Hegel)在他的美學講演中提出的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觀點。在黑格爾看來,隨著理念的發展,它會變得越來越復雜和深邃,以至于完全超出了感性材料或手段的表現范圍,這時我們就只能通過哲學的理性思考才能把握理念,而不能以藝術的感性形式來表現理念,藝術因此為哲學所取代。受黑格爾藝術終結論的啟發,丹托(A. Danto)闡發了一種更為精致的藝術終結論。在丹托看來,藝術發展的歷史就是藝術不斷通過自我認識達到自我實現的歷史,換句話說,是藝術不斷認識自己本質的歷史,藝術發展史的最終目的,就是藝術最終認識到自己是“藝術界”(artworld)的產物,是理論解釋的結果,是一種被理論氛圍(an atmosphere of theory)所環繞的存在。藝術發展的最終目的在20世紀的藝術實踐中已經達到。一旦認識到自己的本性,藝術發展的歷史就走到了盡頭,因為作為理論解釋的藝術其實就是哲學,藝術最終在哲學中終結了自己的發展。今天的藝術處于它的“后歷史”(post-historical)階段,由于藝術的所有可能性已經被實踐過了,因此今天的藝術實踐只是對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各種藝術形式的重復,它已經不可能再給人以驚奇的效果。
丹托的藝術終結理論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主張藝術總是不斷創新的。任何非創新的藝術實踐都只是一種習慣,而不是真正的藝術實踐。20世紀的藝術實踐,窮盡了藝術所有的可能性,因此藝術不可能再向前發展了,藝術的歷史也就終結了。
擺脫藝術終結的最好方式,就是為藝術尋找一個這樣的領域,它能永遠滿足藝術家創新的沖動且在根本上抵制理論的解釋。這個領域就是中國畫所追求的意義世界,一個在概念理解之下或之前的前真實世界。前真實世界是常新的、不可重復的,而且是不能用概念來解釋的。在前真實世界中工作的藝術家不會有影響的焦慮,因為他的工作是唯一的、不可重復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藝術終結之后的藝術,是表現前真實世界的藝術。這并不是說藝術將在形式上向中國畫回歸,而是在精神上去追求中國畫的理想。
我還要更冒險地主張,這種新的藝術方向,不僅對于藝術的自我拯救非常重要,而且有助于人類擺脫生存困境。如果一切都可以用概念來表達,那么就意味著一切都可以被信息化。如果果真這樣的話,人類最終就會變成信息終端。讓我以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所講的一個科幻故事來說明這個觀點。
想像兩個表面上完全相同的觀眾,他們能夠對面前的藝術作品做出完全相同的解釋。其中一個是人類,他為他所看到和解釋的東西而興奮不已。而另一個只是一個經驗不到任何可感知性質的電子人,它感覺不到快樂,實際上根本感覺不到任何情感,它只是為了做解釋陳述而機械地處理感知的和藝術界的數據。由于這個原因,即便電子人的解釋陳述在描述上比人類的解釋陳述要更加精確,我們仍然可以說人類對藝術的一般反應要更為優越,而由于電子人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東西,因此它根本就沒有理解藝術到底是什么。現在進一步想像要是徹底將審美經驗從我們人類文明中剔除出去,那么我們就會完全被改造為那種電子人或者被電子人所滅絕。
舒斯特曼這里所講的那種審美經驗,就是我所說的那種前概念理解,只有突破概念的幕帳我們才能獲得關于事物的在場經驗,而在場經驗又是人生的真正組成部分。在一切都可以被信息化的今天,能夠保持和表現在場經驗的藝術顯得尤其重要,因為這關系到人類的未來:人究竟是進化為信息終端,還是繼續保持血肉之軀?
《清華美術》2006年第2期